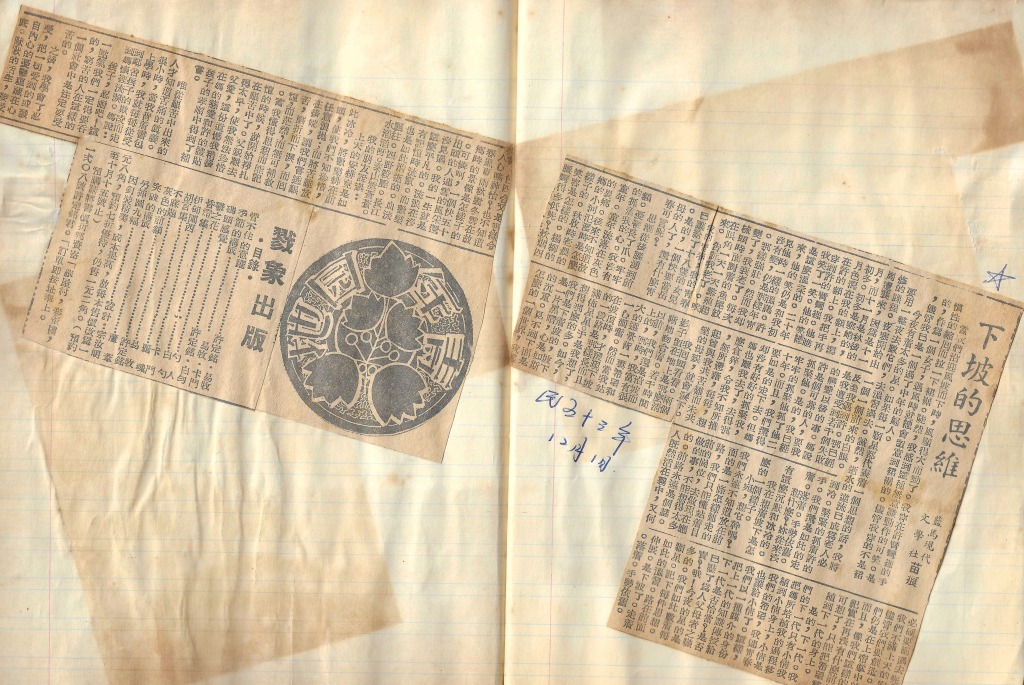當我們沿迎風坡而下時,風顯得大而勁了。我穿在許臂彎裡的手慣性的縮回而拉一下裙裾。陡然,我感到這種無意識動作的可笑。是的,作為一個女子,遇風時就總會留意到裙裾。儘管我穿的不是裙,儘管我已是一個過了中年的婦人。
今夜有着太多的星星。如果每一顆星都代表一個思想的話,我將要用一整夜去數它們,去溫習過去。誠然,逝水的逆流已成為老人必修的課程。夜寒開始由周遭襲來,因為是十一月,而十一月是秋後的初冬,初冬是寒峭的,月色瀉在我的額上,瀉在許的額上。我把手再穿到許的臂彎裡。他瞧我笑了笑。他的笑總是耶麼溫柔的。二十年來,他的笑仍是和我初見他時一樣的溫藹。許沒有變,仍是那樣年青。那樣强壯。然而我卻變了,我衰老了。每次梳頭時面對着的魚尾紋在眼角一天一天繁殖起來。告訴我老了。唉,我的青春,我的青春已讓給十八歲的女兒。是的,一個快要當岳母的人了,還有甚麼青春可言呢?
思潮從後腦湧到前額。憂鬱長了爪。牢牢的抓着我的心。我沒有童年。童年流落在灰色的異鄉。從來不知道故鄉的小河氾濫時是怎麼樣子的。秋收時老農的笑容是怎樣的。楊柳的腰彎得多低呢?炊煙四起和暮色四合又是那樣令入心曠神怡?也不知道春風夏雨秋雲冬雪在故鄉時的景象是怎樣子的。可憐呵,一個快五十出頭的人連雪的風釆還沒見過。我的一生就是這麼平凡的。流浪在沒有記憶時流竄。而歡樂也是如此消逝的。血流飄柱。四野殺聲。長江水滔滔呀。泰山雲蒼蒼。
我的朋友說過:上天的安排竟是如此冰冷,將歡樂排在前頭,使我們不知珍惜,任意浪拋,而將苦難放在後端,譲我們嘗透艱苦,磨折而下淚,而回憶,而茫然,而無可補救。
當我懂得思想而能記憶的時候,就開始掙扎在艱苦中了。父親離去得太早,使我無法珍惜父愛,這份遺憾我稍後在媽的慈愛和許的體貼孩子的孝順中得到了補償。
唯從艱苦中出來的人才知道苦痛的真義。很小時,當我背着書包上學時。我就每每受到鄰舍孩子的欺凌而走到媽懷裡流淚。媽說:
孩子,忍耐吧!這一點氣我們一定得要吞的,窮苦人家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是注定要受苦的。
之後,我學會了忍受,把一切受到的或發自內心的憂鬱蘊藏在心底。默默的生活,接受一個一個前來的白眼。及至我遇到許。那已經是我遭受到若干個失敗戀愛以後的事。媽說許是個可靠的人,要我抓緊他。是的,我已經牢牢的抓了他二十年。而且,我們還得如是的走下去。但媽卻沒有好好的抓緊我,媽也離我去了,去得那麼倉猝,令我不知所措,無所憑藉,每每,想起曾與我共苦難而未共樂的母親,就會淚下。
我回頭看看。兩個影子留在地上是那麼清晰地吻合着。若干時間以前,我們還是沿坡而上的,那時,我富有很美的遠景,背一簍希望和一心興奮。然而當我站在坡頂時,才發現下坡的一段路是那樣長而且滿佈星星。於是我想了,想得那麼多。如今,我們是下着坡了,坡下是一片黑暗,心是如斯的沉重。見不到下面是怎麼的一個世界,我感到冷。緊緊的抓着許的手。我們還是如此的走着。落着。手勢依舊。
想甚麼?妳從來沒有這麼沉默和冰冷的。
我在想着坡下是怎麼的一個樣子。
想它幹嗎?我們永遠不知道放在前面的是一條怎樣難走的路,我們只能站緊目前的崗位,去做現在應做的事,不能想得太多。前路永遠是個謎。人既然活在霧中,又何必硬要衝過去呢?儘管我們不滿上天的安排。儘管我們要創造。但我們仍是在上帝掌中的。而且,像我們這樣的年紀實在再沒有甚麼前途可想了,只能把希望移植到下一代的身上。
是的,下一代。我們的下一代只有小倩,我把媽所培植我的過程移植到小倩身上,小倩是我們的希望,我連青春也讓給小倩了。這樣?我們以一種媒介的身份把上一代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是否恰當?是否已盡了為人父母者之職責?哦!今夜的星星真是多的。我們如此數看每顆星。記下每件思想。如此的溫習。路在前面伸展。是下坡了。走着。落着。手勢依舊。
――1964年12月刊於《星島日報》
(許定銘臉書2023年12月4日)